范若兰的《移民、性别与华人社会:马来亚华人妇女研究(1929-1941)》指出,自中国迁移来马来亚的女性人口,1850年代是初始,1920和1930年代是高峰期。
 这些女性移民,除了被拐卖过来(即所谓猪花)充当性工作者、侍妾、养女,也有因为家贫,或为了逃避枷锁人生(不断生育小孩的人生,无法自主婚姻的人生,对世界一无所知的单调人生)、企盼独立谋生,于是自愿渡海而来,成为贡献劳力的工人,或是教师、女佣、裁缝、理发师等,有的则是跟随丈夫过来、与家人团聚的家庭主妇。
这些女性移民,除了被拐卖过来(即所谓猪花)充当性工作者、侍妾、养女,也有因为家贫,或为了逃避枷锁人生(不断生育小孩的人生,无法自主婚姻的人生,对世界一无所知的单调人生)、企盼独立谋生,于是自愿渡海而来,成为贡献劳力的工人,或是教师、女佣、裁缝、理发师等,有的则是跟随丈夫过来、与家人团聚的家庭主妇。
女性只有串场的陪衬角色?
这一片一百多年的华人女性历史,蕴藏丰富的书写题材,却遭受华文作家忽略。在结构庞大的、气势恢宏的史诗叙事里,或者在精巧的短篇里,女性,往往是一抹模糊的影子,串场的陪衬角色——她们大概就只是出来与男主角谈谈恋爱,在家里扮演贤妻良母,偶尔是施展美人计的间谍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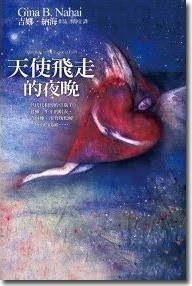 现今常常被小说家当作国族史来书写的长篇小说,其实已成为国际上各族群、各语系(女性)作家书写女性历史的载体。而这样的女性历史叙事,可以超越族群和国家疆域的界限,反思父权体制的固有界定及钳制。在这个时代,人人都具备多重的、充满变化的身份,如此叙事也许更符合现实中的生存状况。
现今常常被小说家当作国族史来书写的长篇小说,其实已成为国际上各族群、各语系(女性)作家书写女性历史的载体。而这样的女性历史叙事,可以超越族群和国家疆域的界限,反思父权体制的固有界定及钳制。在这个时代,人人都具备多重的、充满变化的身份,如此叙事也许更符合现实中的生存状况。
逃离种族和国籍身份的铰链
原以波斯语写作,后来用法文,再改用英文创作的吉娜.B.纳海(Gina B. Nahai),惊世之作《天使飞走的夜晚》就是一部华丽璀璨却又交织着辛酸血泪的女性家族(母族)史。
吉娜.B.纳海是犹太人,在伊朗生长,在欧美国家受教育。《天使飞走的夜晚》的主角天使罗珊娜飞走了,离开自己的家园,更明确地说,她逃走了,逃离种族和国籍身份的铰链,逃离家族中女性宿命的轮盘,最后在“充满选择的国度”(指美国)得到宽恕。
逃离是女性小说的关键词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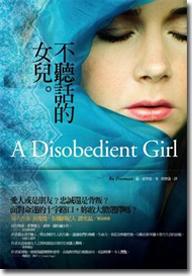 出生于斯里兰卡的茹.富里曼(Ru Freeman),在美国求学及工作,视斯里兰卡和美国为家乡,以英语写作。《不听话的女儿》书写两代女性的爱情和命运。有趣的是,这部小说的关键词也是:逃离。
出生于斯里兰卡的茹.富里曼(Ru Freeman),在美国求学及工作,视斯里兰卡和美国为家乡,以英语写作。《不听话的女儿》书写两代女性的爱情和命运。有趣的是,这部小说的关键词也是:逃离。
印裔美籍诗人及小说家奇塔.蒂娃卡鲁尼(Chitra Banerjee Divakaruni ),书写主题涵盖女性、移民、神话、南亚历史等。她的《香料情妇》及《我心姊妹》皆为畅销小说,被改编成电影和连续剧。多重交叠的身份,使她着重也擅长描绘女性移民的处境。
流亡也许是人生最好经历
吉娜.B.纳海在《天使飞走的夜晚》尾声的一段叙述颇有意思:“我这一辈子都在流亡,连还在自己家里的时候也不例外。对于流亡人生,我深有体会:随便你要怎么爱你的故国都可以。有时候,流亡甚至可以说是我们人生之中最好的经历。”
人生之中最好的经历,何不正面迎向?因此,家国在何方,如今也不是那么重要的问题了。

